

感謝您使用 Virsody 虛擬體驗服務
升級方案解鎖無廣告版本30 秒後可關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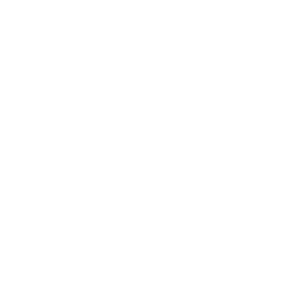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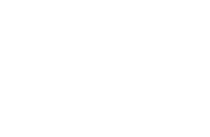 Use keyboard or panel to move
Use keyboard or panel to move Use mouse or drag to rotate
Use mouse or drag to rotate觀看次數: 1.2k・ 3年前

近代台灣表演藝術的舞台隨著不同文化介面的媒合、藝術形式的多元發展,逐步形構出一組越趨雜揉的複調語境;在原住民藝術的場域中,變裝(drag)表演的出現,或許是近年來最令人驚艷、也最驚愕的現象之一。 相較於過去的原住民藝術創作者,慣常透過創作與其母體文化或場域進行各種銜接,台灣原住民變裝皇后(Drag Queen)不只在表演形式上看似與傳統的樂舞文化幾乎脫節,而是承繼了西方自上世紀以來男同志地下文化中的娛樂表演,他們所現身之處,也幾乎悖離著原鄉故土,而是高度城市化的暗夜時間、霓虹四射的妖嬈舞台。然而在當代的全球原民研究中,「跨性」與「變裝」作為一種現象,早有其歷史依據,例如北美洲的雙靈(Two-spirit)文化,以及南島語系部分島嶼中的跨性別乃至於多性別角色。不過弔詭的是,在台灣的殖民檔案中,幾乎找不到任何原住民的跨性與變裝表象,當其他地域的原住民變裝藝術已開始連結某種越趨正典的文化論述,台灣原住民的變裝表演卻好似依附在另一群體的經驗之中,成了一種輕薄的混生物種,前身不明、今世尚淺,歷史沒有重量,意義遠在他方。 然而如若我們脫開對於文化正統性的偏執,回望台灣上一世紀的「島內移工」史,會發現早在近三十年前、早於「變裝皇后」其表演脈絡與藝術類型被翻譯進入本土之前,台灣新興的原住民社群中就已經開始出現類似於這種變裝表演的現象。彼時台灣社會在全球冷戰結構中迎來整體經濟的轉向,族人離鄉背井,去到大城市工作、賺錢。在這一代島內移工中,除了從事基本的勞力工作,還有一些人開始透過表演,在各種場合或為交際、或為謀生。爾後這批表演者有的在1990年代回到家鄉,帶著在大城市裡的表演經驗、甚或是異質性極高的性別身體,繼續在部落裡操持故業,成了原鄉社群的某種日常風景、直到今天。「原住民變裝表演」的脈絡,或許並不在正典的文化史中,它所映照的,極有可能是原住民移工史裡一塊被遺忘的碎片,它拼湊著帝國經濟殖民下的底層紋路,是上世紀一部分原住民性少數早已遭逢的處境。 而今,「離鄉背井」可能有了新的意含。1980-1990年代出生的原住民青年,在離開結構緊密的親緣場域或部落社會以後,城市空間成了過往陰蔽身體的解放所在,「變裝表演」也擦去了底層色彩,隨著當代文化的推進,成了專門技藝、乃至於性少數族群的自我賦權。然而在這前後兩代甚至三代的差異情境中,是否可能徵示著某些相同或相異的情感或美學結構?變裝表演者如何回望自己的原住民身體、並在這樣的認同中回應著怎樣的歷史和未來?「后古事紀」建立在約50年的時間跨度之間,試圖透過三位表演者:1970年代離鄉北上的巧克力(布農族)、1990年代出生的飛利冰(Feilibing IceQueen/布農族)與羅斯瑪麗(Rose Mary/泰雅族),拼湊一幅被過去的原住民文化場域遺落的變裝表演叢像。在這樣的叢像中,我們或許得以重新檢視某種族群史觀的建構法則,以及在這一套法則之外的異質身體、游移在斷裂和重接之間的美麗與哀愁,蝶變與轉生。 -后古事紀:當代原住民變裝表演叢像- 展期:Oct. 1- Nov. 31 地點:PulimaLink 策展人:呂瑋倫 藝術家:巧克力、飛利冰Feilibing IceQueen、羅斯瑪麗Rose Mary

0 則留言